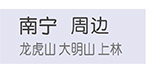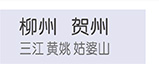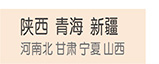在我最难忘的假期的时刻与我的孩子们是电话我由一个顶峰,在大蒂顿国家公园一个夏天。男孩们7和10,他们没有送往壮丽景色与相当热情我所希望的。我相信这个词“无聊”是发出一次或两次,有人抱怨道“我们到了吗?”
这给了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阿尔卑斯山,不提顿山脉,但同样缺乏升值从后座。“你能至少咕哝着说你的升值,所以我知道你还在那儿?”我的父亲问,我的兄弟姐妹,我就这么做了,那座山,再向下。
这就是我来叫我爸爸从怀俄明州山顶——和道歉。
旅游与孩子们并不总是一张明信片。到达那里的,在那里,回到家里。这涉及到齿轮、规划和耐心,在你开始之前无法想象的数量将他们前进。
然而,我的父母和他们坚持不懈,带我们几个星期每年夏天。他们带着我们穿过包一个单独的手提箱来招待他们在飞机上舞台。他们没有放弃在“苦修什么比在公共场合里与我的父母为什么能不我只是呆在家里年。下个月我们将聚集在
新奥尔良对我母亲的75岁生日,孩子们和配偶在一起。
我一直很高兴他们“拖”我到地极,但直到一天,我完全明白我很感激。在那之前我只考虑什么
旅行给了我作为一个个体——舒适的感觉在新的地方,知识,有一个大大的世界。我的电话,我父亲是我第一次欣赏什么样的旅行给了我们作为一个家庭。
我们从来没有更多的家庭比当我们不在家。每天在后面的一个汽车租赁,每天晚上的谈判,得到了床,我弟弟、妹妹和我成为一个单位,依靠彼此娱乐(见鬼,电视说不同的语言)。回家我们有单独的轨道——不同的朋友、老师、活动、卧室。走,我们在同步。在彼此的方式很多,是的。呼噜的一些时间,真。而且我们还以为溶解在沉默笑声之间的咕哝上山,很高兴在我们的私人玩笑。
“对不起,”我说到我的父亲25年后在一个容易破裂的手机打电话,而我的儿子从怀俄明,释放了从后座,爬过岩石。
“这是我最喜欢的记忆,”爸爸回答道。现在,我想,它是我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