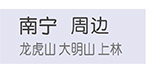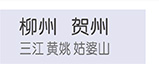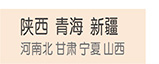我们旅行游玩,比作意义上的“我要离开这里,”换换空气,启迪,为大庸俗自吹自擂是遥远的,被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偷窥的浪漫的异国直瞪瞪地看着;有时我们旅行,因为我们已被赶走。我被驱逐一次,它强化了我。
在令人窒息的,车内的演讲大厅1960年代的新加坡,我是一个未足额支付大学讲师,其中一个文本我教是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这让我保持乐观和发挥提供了支撑解药嘲笑的假设(“理发”、“戒烟”、“你是个嬉皮”),盛行于微小的排外(当时)岛。
罗马将军,科里奥兰纳斯,大胆但未被欣赏的,一个精英主义者,你会说,一个有教养的人说他的脑海里,所以他是从
罗马放逐强劲。远非狼狈,他谴责黑帮说:“… 因此我把我的背:有一个世界其他地方。”这成了我的口号在城邦小国,都反对我。如果我一个盾徽和一个铭牌,我的一个传令官的元素是,座右铭。在我三年的合同并不是新的我离开,一直走。
我的愿望列表的地方不仅是漫长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显而易见。是的,我去过巴塔哥尼亚和刚果和锡金,但我还没去过美国最美丽的,从不到阿拉斯加、蒙大拿、爱达荷州和南达科他州,我只有最最瞥见堪萨斯和爱荷华州。 我想看他们,而不是乘坐但旅行慢慢在地面上,保持支持公路,公然的一般规则从不吃到了一个地方,叫妈妈的,从不玩一个叫医生。
什么也没有对我有多兴奋在它比经验不断上涨的清晨在我自己的房子和进入我的车,开车走在一个漫长、曲折的旅程通过北美。地球上没有多少能打败它在旅行一个自由的意识——没有搜身检查,没有护照,没有机场混乱,就旋转一个引擎,然后“吃我的尘埃。长,即兴的公路
旅行的车是典型的美国。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了这样一个旅行在1918年的跑车,从康涅狄格州到阿拉巴马州在1920年,三个月后他们的婚姻。 斯科特写到一个活泼的账户,游轮的滚动垃圾,最近发表一个简短的书。
我从来没有去过不丹,愿意去,因为它的架构和它的古老的虔诚,来验证其国民幸福总值指数。我有朋友在塞舌尔我从来没有访问,希望看到。除了著作的保罗鲍尔斯和塔希尔沙,摩洛哥炖菜我已经在餐馆,我不知道很多关于摩洛哥。我将是一个绝对初学者在也门,马达加斯加和塔斯马尼亚岛,这是在我的列表。在一个旅游幻想我骑自行车数周通过一个大,稍平的国家——澳大利亚,或者中国南方。在另一个梦我在一个滑雪豆儿在南极洲的一个地方,我读过的关于童年以来,从未去过。